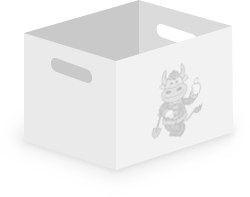托尔斯泰
展开


我像一只蹲在井底的青蛙
生命短暂,转瞬即逝,
有什么东西能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?
而且这种意义不会被贫穷、痛苦、死亡摧毁?
出现了矛盾,摆脱这个矛盾只有两条出路:要么就是我认为理性的东西并没有我想的那样理性;要么就是我觉得不理性的东西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不理性。我开始验证自己得出理性知识的推理过程。
验证推理过程时,我发现它完全是正确的。不可逃避的结论就是,生命是虚无的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错误,错误在于我推理的过程和我提出的问题并不一致。问题还是那个:我为什么而活?也就是在我虚幻缥缈转瞬即逝的生命中,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地永恒不灭?在这大千世界中,我这有限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?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我开始参悟生命。
显而易见,目前所有生命问题可能的答案都不能使我满意,因为不管乍一看我的问题多么简单,但是它却要求用无限来解释有限,或者用有限去解释无限。
我的问题是:我的生命具有怎样的超越时间、空间、因果联系的意义?我的回答则是:我的生命在时间、空间、因果联系上又有何意义?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,答案就是毫无意义。
在论证的过程中,我经常把两个概念进行比较,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途径了。比如对永恒与永恒进行比较,有限与有限进行比较,因此我能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:力量就是力量,物质就是物质,意志就是意志,永恒就是永恒,没有就是没有。仅此而已,更深的结论再也得不出了。
在数学中也经常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,当你想解方程的时候,解的却是恒等式。论述的方法是对的,但是结果却得到:A=A,或者X=X,或者0=0。在我论证生命意义的问题时,也出现了这种情况。对于这个问题,所有科学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个恒等式。
的确,认知很严格理性。笛卡尔得出的这些认知,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。抛开所有人类基于信仰的知识,在理智和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建一座认知的大厦。对于生命问题,除了我之前得出的那个不明确的答案外,不可能再得出另外的答案,这个答案正是我之前获得的,是一个不明确的答案。开始我以为,认知会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,叔本华的答案——生命没有意义,它是罪恶。但是经过研究我发现,这个答案不是肯定的,只是我主观想把它表述成这样。答案表述得非常严密,和所罗门、叔本华、婆罗门给出的答案一样,只不过是一种不明确的答案,或者是恒等式:0=0,生命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展现的,就是虚无。因此哲学界什么也没有否定,只是说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,对于他们来说,答案仍旧是不确定的。
参透了这些之后我明白了,不可能在理性的认知中找到我问题所需的答案,理性的认知所给出的答案只是表明,只有在另一种提问方式中,只有在推论中引入有限与无限之间关系的问题时,才可能有答案。我明白了,无论信仰给出的答案有多么匪夷所思,甚至是扭曲的,它们都有一个优点,就是每一个答案都引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,没有这一点,就不可能有答案。
无论我怎样变着花样地问“我该怎么生活”这个问题,回答都是:“根据上帝的旨意生活。”从我的生命中会沉淀出什么真正的东西?——无尽的痛苦或者是无穷的快乐。哪一种意义是死神不能带走的?和万能的上帝融为一体,那就是天堂。
因此,除了之前我认为是唯一理性的知识以外,我不得不承认,在当下全人类中还有一种非理性的知识,那就是信仰,它提供生的可能。
这些信仰对于我来说,还是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,但是我不得不承认,只有这种信仰能够回答人类生命的问题,从而使生存成为可能。
理性的认知使我承认,生活毫无意义,我的生活变得停滞不前,我想销毁自己。纵观整个人类,我发现,人们往往都是一边生活,一边宣称自己知道生命的真谛。我又把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,在我活着的时候,我已经知道了生命的真谛。就像对其他人一样,这种信仰也给予我生命的意义和活下去的机会。
进一步观察其他国家的人们,与我同一时代的人以及前人,我发现情况完全相同。但凡有人的地方,必定有信仰,从有人的那天起,它就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可能,无论何时何地,信仰的主要特征都一样。
无论何种信仰给什么样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,任何一个答案都能赋予人类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,这种意义不能被苦难、贫穷和死亡所摧毁。也就是说,只有在这种信仰中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可能。那么,什么是信仰?我明白了,最纯粹的信仰不仅仅只是“揭示无形事物”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,不仅仅是神的启示(它仅仅是信仰其中的一个特征描述),不仅仅是人与上帝的关系(应该先确定信仰,而后确定上帝,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确定信仰),不仅仅是认同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容易理解的信仰(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信仰的)——信仰就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认知,因为有这种信仰,人类才给予自己一条生路,活了下来。信仰就是生命的力量。如果一个人活着,他肯定坚信着某些东西。如果他不相信人是为了某些东西而活,那么他活不下去。如果他看不到,也不明白这种有限的虚无缥缈,他就会相信这种有限。如果他明白了这种有限的虚无,那么他就会信仰无限。没有信仰,就不能生存。
回想起自己的内心活动,不由得毛骨悚然。如今我明白了,一个人为了能活下去,他需要对无限视而不见,或者把有限和无限联系起来解释生命的意义。我曾这样解释过生命的意义,但是在我还信仰有限,并且用理智去检验它时,这种解释我是不需要的。在理性的光辉下,先前所有的解释都化为了灰烬。我停止信仰有限的日子还是到来了。于是我在理性的基础上,用我所知道的一切去得出一种能说明生命意义的解释,但最终却是一场徒劳。我和人类最优秀的思想界得出了相同的结果:0=0,得到这样的结果令我感到非常惊讶。那时也就只能这样,别的结果也得不出来。
当我在实验科学中寻找答案时,我做了些什么?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活着,为此我学研究了除我以外的所有东西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知道了很多,但是这里却没有我需要的。
当我在哲学科学中寻找答案时,我做了些什么?我研究了一些人的思想,这些人和我有着相同的境遇,他们同样不能回答“我为什么活着”这个问题。显然,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,是我早就已经知道的。也就是说除此之外的知识不可能被获得。
我是什么?是无限的一部分。要知道在这几个字中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问题。
难道人类在昨天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吗?难道在我之前,就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简单、每个聪明的小孩子都能提出的问题?
要知道,这个问题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;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,就已经明白了,要想解决这个问题,只是把有限和有限进行比较、无限和无限进行比较是不够的;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,就已经发现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,并且已经表述出来了。
在上帝、自由、善良这些概念中,把无限和有限进行比较,就会得出生命的意义。这些概念虽然经过我们逻辑上的检验,却经不住理性的批判。
我们像孩子一样,无知又任性地把一座钟拆开,取出发条做成玩具,然后非常惊奇地发现钟不走了。如果这件事称不上可怕,至少很可笑吧。
需要解决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来回答生命的问题,这么做很重要。只有解决和回答了这些问题,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。这是我们在任何时间、地点,在任何民族能找到的唯一解决途径,是时间的产物。人类的生命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,它来之不易,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与之类似的解决办法。而我却轻率地推翻了这种解决办法,为的是再次提出任何人都有的,而我们又不能解答的问题。
永恒的上帝、神圣的灵魂、人间的事与上帝的关系、道德上的善良与罪恶,所有这些概念都隐藏在我们不知道的古老的人类历史中,如果没有这些概念,就不会有生命,也不会有我的存在。我却抛开了历代人民的劳动成果,试图自己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,一个新的方式去重新解决这些问题。
那时候我并没有这么想,但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已经在我脑海里落地生根了。我明白,首先,尽管我、叔本华和所罗门都是智者,但是我们却站在了一个愚蠢的地方,我们明白生命就是罪恶,但是我们依然生活着。这简直是蠢到了极点,因为如果生命是非理性的,而我依旧追逐所有理性的东西,我就必然要毁掉这种生命,那就没有人能否定我的结论了。其次,我明白,我们所有的论证,仿佛中了“鬼打墙”,一直在转圈圈,就像一个没有固定住的车轮,再多再好的论证,都给不了我们答案,永远都是0=0。所以,我们的路可能是错的。最后,我逐渐明白,信仰所给的答案中蕴含着人类最高深的智慧,我没有权利基于理性而否定这些答案,最重要的是,只有这些答案能回答生命的问题。
生命短暂,转瞬即逝,
有什么东西能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?
而且这种意义不会被贫穷、痛苦、死亡摧毁?
出现了矛盾,摆脱这个矛盾只有两条出路:要么就是我认为理性的东西并没有我想的那样理性;要么就是我觉得不理性的东西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不理性。我开始验证自己得出理性知识的推理过程。
验证推理过程时,我发现它完全是正确的。不可逃避的结论就是,生命是虚无的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错误,错误在于我推理的过程和我提出的问题并不一致。问题还是那个:我为什么而活?也就是在我虚幻缥缈转瞬即逝的生命中,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地永恒不灭?在这大千世界中,我这有限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?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我开始参悟生命。
显而易见,目前所有生命问题可能的答案都不能使我满意,因为不管乍一看我的问题多么简单,但是它却要求用无限来解释有限,或者用有限去解释无限。
我的问题是:我的生命具有怎样的超越时间、空间、因果联系的意义?我的回答则是:我的生命在时间、空间、因果联系上又有何意义?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,答案就是毫无意义。
在论证的过程中,我经常把两个概念进行比较,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途径了。比如对永恒与永恒进行比较,有限与有限进行比较,因此我能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:力量就是力量,物质就是物质,意志就是意志,永恒就是永恒,没有就是没有。仅此而已,更深的结论再也得不出了。
在数学中也经常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,当你想解方程的时候,解的却是恒等式。论述的方法是对的,但是结果却得到:A=A,或者X=X,或者0=0。在我论证生命意义的问题时,也出现了这种情况。对于这个问题,所有科学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个恒等式。
的确,认知很严格理性。笛卡尔得出的这些认知,是从怀疑一切开始的。抛开所有人类基于信仰的知识,在理智和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建一座认知的大厦。对于生命问题,除了我之前得出的那个不明确的答案外,不可能再得出另外的答案,这个答案正是我之前获得的,是一个不明确的答案。开始我以为,认知会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,叔本华的答案——生命没有意义,它是罪恶。但是经过研究我发现,这个答案不是肯定的,只是我主观想把它表述成这样。答案表述得非常严密,和所罗门、叔本华、婆罗门给出的答案一样,只不过是一种不明确的答案,或者是恒等式:0=0,生命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展现的,就是虚无。因此哲学界什么也没有否定,只是说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,对于他们来说,答案仍旧是不确定的。
参透了这些之后我明白了,不可能在理性的认知中找到我问题所需的答案,理性的认知所给出的答案只是表明,只有在另一种提问方式中,只有在推论中引入有限与无限之间关系的问题时,才可能有答案。我明白了,无论信仰给出的答案有多么匪夷所思,甚至是扭曲的,它们都有一个优点,就是每一个答案都引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,没有这一点,就不可能有答案。
无论我怎样变着花样地问“我该怎么生活”这个问题,回答都是:“根据上帝的旨意生活。”从我的生命中会沉淀出什么真正的东西?——无尽的痛苦或者是无穷的快乐。哪一种意义是死神不能带走的?和万能的上帝融为一体,那就是天堂。
因此,除了之前我认为是唯一理性的知识以外,我不得不承认,在当下全人类中还有一种非理性的知识,那就是信仰,它提供生的可能。
这些信仰对于我来说,还是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,但是我不得不承认,只有这种信仰能够回答人类生命的问题,从而使生存成为可能。
理性的认知使我承认,生活毫无意义,我的生活变得停滞不前,我想销毁自己。纵观整个人类,我发现,人们往往都是一边生活,一边宣称自己知道生命的真谛。我又把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,在我活着的时候,我已经知道了生命的真谛。就像对其他人一样,这种信仰也给予我生命的意义和活下去的机会。
进一步观察其他国家的人们,与我同一时代的人以及前人,我发现情况完全相同。但凡有人的地方,必定有信仰,从有人的那天起,它就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可能,无论何时何地,信仰的主要特征都一样。
无论何种信仰给什么样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,任何一个答案都能赋予人类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,这种意义不能被苦难、贫穷和死亡所摧毁。也就是说,只有在这种信仰中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可能。那么,什么是信仰?我明白了,最纯粹的信仰不仅仅只是“揭示无形事物”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,不仅仅是神的启示(它仅仅是信仰其中的一个特征描述),不仅仅是人与上帝的关系(应该先确定信仰,而后确定上帝,而不是通过上帝来确定信仰),不仅仅是认同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容易理解的信仰(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信仰的)——信仰就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认知,因为有这种信仰,人类才给予自己一条生路,活了下来。信仰就是生命的力量。如果一个人活着,他肯定坚信着某些东西。如果他不相信人是为了某些东西而活,那么他活不下去。如果他看不到,也不明白这种有限的虚无缥缈,他就会相信这种有限。如果他明白了这种有限的虚无,那么他就会信仰无限。没有信仰,就不能生存。
回想起自己的内心活动,不由得毛骨悚然。如今我明白了,一个人为了能活下去,他需要对无限视而不见,或者把有限和无限联系起来解释生命的意义。我曾这样解释过生命的意义,但是在我还信仰有限,并且用理智去检验它时,这种解释我是不需要的。在理性的光辉下,先前所有的解释都化为了灰烬。我停止信仰有限的日子还是到来了。于是我在理性的基础上,用我所知道的一切去得出一种能说明生命意义的解释,但最终却是一场徒劳。我和人类最优秀的思想界得出了相同的结果:0=0,得到这样的结果令我感到非常惊讶。那时也就只能这样,别的结果也得不出来。
当我在实验科学中寻找答案时,我做了些什么?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活着,为此我学研究了除我以外的所有东西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知道了很多,但是这里却没有我需要的。
当我在哲学科学中寻找答案时,我做了些什么?我研究了一些人的思想,这些人和我有着相同的境遇,他们同样不能回答“我为什么活着”这个问题。显然,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,是我早就已经知道的。也就是说除此之外的知识不可能被获得。
我是什么?是无限的一部分。要知道在这几个字中已经包含了全部的问题。
难道人类在昨天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吗?难道在我之前,就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简单、每个聪明的小孩子都能提出的问题?
要知道,这个问题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;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,就已经明白了,要想解决这个问题,只是把有限和有限进行比较、无限和无限进行比较是不够的;从人类产生的那天起,就已经发现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,并且已经表述出来了。
在上帝、自由、善良这些概念中,把无限和有限进行比较,就会得出生命的意义。这些概念虽然经过我们逻辑上的检验,却经不住理性的批判。
我们像孩子一样,无知又任性地把一座钟拆开,取出发条做成玩具,然后非常惊奇地发现钟不走了。如果这件事称不上可怕,至少很可笑吧。
需要解决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来回答生命的问题,这么做很重要。只有解决和回答了这些问题,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。这是我们在任何时间、地点,在任何民族能找到的唯一解决途径,是时间的产物。人类的生命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,它来之不易,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与之类似的解决办法。而我却轻率地推翻了这种解决办法,为的是再次提出任何人都有的,而我们又不能解答的问题。
永恒的上帝、神圣的灵魂、人间的事与上帝的关系、道德上的善良与罪恶,所有这些概念都隐藏在我们不知道的古老的人类历史中,如果没有这些概念,就不会有生命,也不会有我的存在。我却抛开了历代人民的劳动成果,试图自己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,一个新的方式去重新解决这些问题。
那时候我并没有这么想,但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已经在我脑海里落地生根了。我明白,首先,尽管我、叔本华和所罗门都是智者,但是我们却站在了一个愚蠢的地方,我们明白生命就是罪恶,但是我们依然生活着。这简直是蠢到了极点,因为如果生命是非理性的,而我依旧追逐所有理性的东西,我就必然要毁掉这种生命,那就没有人能否定我的结论了。其次,我明白,我们所有的论证,仿佛中了“鬼打墙”,一直在转圈圈,就像一个没有固定住的车轮,再多再好的论证,都给不了我们答案,永远都是0=0。所以,我们的路可能是错的。最后,我逐渐明白,信仰所给的答案中蕴含着人类最高深的智慧,我没有权利基于理性而否定这些答案,最重要的是,只有这些答案能回答生命的问题。
关联的话题与分类


声明: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所发内容承担法律责任,倡导理性交流,远离非法证券活动,共建和谐交流环境!